
诗,便是用词语去接触国际。但咱们的语词还能真挚地接触和调查这个国际吗?阿莱士·施蒂格的诗篇,或许就在做这样接触国际的尽力。
这位斯洛文尼亚诗人、散文家和小说家,是新一代斯洛文尼亚文坛新秀,最富原创力的欧洲今世诗人之一。一起仍是德国言语文学研究院柏林艺术研究院院士,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取得者,著作被译成英语、德语和法语等十六种文字。
阿莱士·施蒂格,斯洛文尼亚诗人、散文家和小说家。
在《从创伤另一端》中 ,收录了作者于1997年至今创造的诗篇及诗词散文著作近百首,别离选自诗集《喀什米尔》等。还附有被誉为“今世歌德”的闻名德国诗人格林拜恩等编撰的诗评。
诗集的风格或滞碍传统的意象构成逻辑,引进奇特的动机;或扮演联觉的体操,精深运用诡论式的叙说;或欣然接受偏僻的句法,在言语和前史的陌生化遇合里寻找词的迷宫的进口,寻找事物和身体在那里的相遇之场所。出现今世全球化语境下,详细个人的细腻感触和体会。
撰文 | 项品超 黄家光
“巩固的国际已云消雾散”?
诗好像便是用词语去接触国际,这个国际可所以咱们的身体,也可所以自然界,不仅是物体,也可所以咱们的举动,咱们的爱恨情仇,总归,事事物物。但咱们的语词还能真挚地接触和调查这个国际吗?在我看来,这也是斯洛文尼亚诗人施蒂格想去处理的问题(之一)。
用诗来接触国际。
与初民不同,在咱们这个年代,咱们现已无法单凭一腔热心和纯情写作哪怕一首真挚的诗了,咱们能够幻想《诗经》中那些质朴之歌,爱恨直从胸中涌出,不违人心亦不违天道。但与那时分的国际图景不同,咱们失掉了脚下坚实的大地。正如格林拜恩在点评施蒂格时分所言:
言语经由那组织了人类仇视并带来逝世和损坏的极权主义意识形状,被前史拖拽着穿过了20世纪之后,在全部那些所发作的恐惧经历之后,诗人已不再能置他的业务于一种安定的基础上。
用施蒂格自己的话说,“全部那些告知咱们自我为何的全部已失掉稳定性”(《照样,当我转过街角》)。以巩固的国际图景作为确保,咱们说什么和怎样说好像都不是问题,但现在,全部巩固的东西都已云消雾散,说什么和怎样说就撕裂成了两个东西,咱们真挚的表达,在说出口的那一刻或许就现已变形歪曲,咱们口吐莲花,它却可能成为利箭射穿别人。这是一方面的困难。
另一方面的困难,来自一个愈加形而上学的理由:咱们信任咱们的语词和国际,或说身体,处在一种不对等的联络之中,语词好像意味着更少的东西,而身体或国际意味着更多的东西。心中五味杂陈,而到口中,仅仅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。语词能言说的好像总是太少,得鱼忘筌,满意就应该忘言。六合有大美而不言,大悲亦复如是。如此看来,咱们陷入了两层的窘境里:一方面,咱们的言说失掉了支撑,变得可疑,另一方面,咱们所说的是那么少,而丢失的是那么多。
身体,是人与国际的创伤
但或许咱们轻视了言语,或说轻视了言语对咱们的含义,特别是诗对咱们的含义:
《那时》
“每个人
都曝露于
他自己
仅有的言语中”
“有时身体
成为
词……身体需求词
来令
其他
身体
知情”
脱离言语,咱们的身体、国际都是不行见的。这种玄乎的说法,更直白的表达是:关于它们,咱们是视若无睹或视若无睹的。这样一种言语观也几乎是现代诗篇的底线一致:是言语在说人,而不是相反。
《从创伤另一端》,阿莱士·施蒂格 著,梁俪真 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
但仅仅如此,咱们仅仅知道言语要言说人,怎样言说,站在什么方位言说是适宜的,这个问题仍然令人疑问。咱们能否站在旷野上呼号,向天主求救?咱们能否站在爱人耳垂边低低絮语,表达诚心?这样的行为怎么不沦为一种不自知的扮演?施蒂格给出的计划是,“从创伤另一端你睁开眼”:
《刮擦器》
当它荡然无存
你睁开眼
像那个时刻的母亲
从创伤另一端你睁开眼
诗人把创伤了解为我(主体、言说者)与身体或国际之间的中介,其实,身体就能够视为人与国际的“创伤”,创伤不是你自动取得的,而是一次意外,一个偶尔,是国际或身体对你的粗犷的进入,从这个创伤你体会到、目击着身体或国际,但你体会到的、目击到的不是一个独立的“物”,比如说你不是体会到、目击到一个与你无关的雨伞、蚂蚁等等,而是体会到、目击到一件事,创伤便是“事”的痕迹。创伤意味着许多许多,可是脱离创伤,什么都将不再持留。所以对施蒂格来说,“事事物物”的要点显然是在“事”上,而诗便是对创伤上“所见所闻”的记载:
《蚂蚁》
它之所是,并没有姓名。
当它消失进它的迷宫,只剩下期望,
期望至少会有几个姓名,称号它所不是。
由于咱们并没有对“物”的命名,而是对“事”命名,而创伤既是迷宫的进口,也是迷宫的出口,连接着言说者和身体或国际。所以,咱们好像应该把凝结的物看作是结疤的创伤,咱们不能经过一个“名词”来掌握身体或国际,而应该经过“动词”来掌握“事”,即经过“物”注视“事”。这样“他就将它们提交给言语范畴”(格林拜恩),并且事总是在时刻和前史中打开的,所以“并不存在不具有前史化含义的物体”(格林拜恩)。这其实也解说了为何施蒂格晚近的诗篇转向文明政治范畴,事总是前史的事。在欧洲,前史总是缠绕着政治、宗教等等(如《站立在你的王国的边境》)。
创伤,是言语和国际的切面
从创伤另一端注视,不是也不行能是跳到国际或身体的方位看,这只不过是一种假托的第三人称。经过创伤让事物自己出现出来,不是一种肯定含义上的事物以自己的言语出现出来。根本就没有一种事物本身的言语,创伤的自我出现是经过人的言语出现出来的,因此是经过人的,咱们总是从人的态度来看和感知这个国际。但与人相关的,和以人为中心的是两回事,这个进程能够被描绘为“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拟人论”(罗科·本钦),这是一种态度的改变,人类中心主义以为国际依赖于人的感知,这种态度推到极致将得出,言语根本上不受约束,而拟人论则将人与物织造在一个不行分的网络之中。
咱们能够看到,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背面,是一种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分立的知道论和表征主义的言语观。简略地说,主客二元敌对的知道论以为自我(心灵)和国际是两个分立的存在序列,知道便是主体对客体投射到心灵之镜中的形象、观念的了解;而言语便是对这种形象、观念的记载,也便是说言语是目标的表征。这样言语和国际就彻底归于两个范畴了,怎么确保言语可靠地记载了目标?不仅如此,乃至当咱们只能经过言语来知道国际的时分,国际的存在与否都是可疑的,怀疑论的鬼魂如影随形。
这样一些哲学问题,对施蒂格来说并不是外在的,他的诗篇写作充满着镇定的思辨,不少诗篇中直接探究词语与目标的联络,接续着玄学派诗人的传统,他“反思了全部这全部”(格林拜恩)。主客二元敌对的知道论和表征主义的言语观,问题在于把主体(人)自外于国际,这便是说,进行知道的人不是在这个国际之外进行知道活动的,两个之间有一个裂缝,所以难以将自我和国际一致起来,言语好像总意味着对事物的不彻底的记载,乃至是过错的记载。
但当咱们把人和国际看作是一个相似性的网络,言语和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知道论和本体论上的距离,而是说它们原本便是接连的,事物总是现已概念化了的,言语化了的,如此咱们的言语就能够去提醒事物内部的信息了。这个进程中,尽管咱们运用言语去提醒“工作”,但言语不是对工作的表征,而是和工作交融在一起的,因此就没有如此这般的距离了。并且由于工作不能脱离言语,如海德格尔所言,言语是存在之家,“存在”有必要要在言语中存在,所以脱离言语,工作就无法显现出来,因此它在咱们日子于其间的含义国际里,根本便是无含义的存在,在这个含义上,咱们能够说工作并没有多于言语的东西,但这不等于说言语能够代替工作,他们相须而不行别离。
这样一种言语观,还有一种泛灵论的形状,咱们能够符咒为例。符咒是言语,但其与事物会有实践的详细的联络,即符咒不是像镜子相同洞照目标,而是实践的对事物产生影响,事物与言语之间是实在的联络,言语就在国际之中:
《以笔直的方法》
人类的魂灵与污水
遵照相同的规矩分支分布
那架照相机……
照相机沉降得历来不行深
它们应已永远地深陷在了竖井里
《瘿瘤》
创伤便是言语和国际的切面,它归于言语,也归于国际,咱们看待国际的当地,就在国际之中,
就深陷在竖井里:
记载创伤,愈合
这个国际的破损具有的姓名
《沙洲》
由于唯有如此,才干使:
那持久藏匿在景深无法被辨认的
涌到外表。成为外表。
《沙洲》
也唯有如此,咱们才干:
穿过榜首扇门进入一个存在着的国际,
穿过同一张第二扇门进入并未存在的国际。
跋文:本文的写作部分获益于杜尔斯·格林拜恩、罗科·本钦的文章及北大一次关于施蒂格的研讨会的录音稿,特此称谢。
作者 | 项品超 黄家光;
修改 | 董牧孜;杨雅冰;张婷、李永博
校正:翟永军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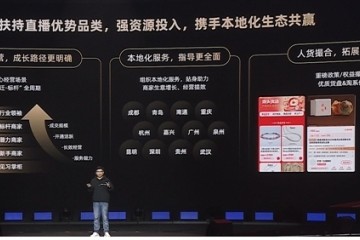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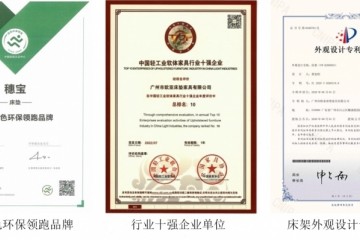



 满足消费者精细化需求,威乐水家电助力把好全屋净水第一关
满足消费者精细化需求,威乐水家电助力把好全屋净水第一关 





